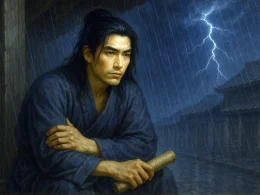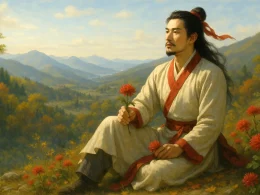「将进酒」
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赏析:
这首诗作于李白被“赐金放还”八年后,与友人岑勋、元丹丘登高宴饮之时。此时诗人年届五十,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其狂放不羁的言行下,是巨大的生命焦虑与精神苦闷。《将进酒》正是这种复杂心绪的火山式喷发,它将怀才不遇的愤懑转化为对生命密度的极致追求,成为一曲用绝望谱写的生命赞歌。
第一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你难道没有看见,那黄河之水仿佛从天而降,奔涌向海,永不复返?
开篇以横绝太空的宇宙视角,将黄河的物理流动升华为时间与命运的象征。“天上来”三字,赋予河流以神性,其壮阔的背后,是无可挽回的宿命感,为全诗奠定了苍茫悲壮的基调。
第二联:“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你难道没有看见,在高堂明镜前悲叹白发丛生,清晨还如青丝,傍晚已似白雪?
镜头从宇宙宏景骤降至私人空间,以极致的夸张压缩个体生命历程。“朝”与“暮”的对比,非写实之语,而是内心焦灼感的物化,将时间流逝的恐怖感推到极致,完成了从空间到时间、从宇宙到人生的过渡。
第三联:“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人生得意之时就应纵情欢乐,切莫让金樽空对明月。
在前两联的巨大压力下,此联是逻辑的必然反弹。“须尽欢”并非浅薄的享乐主义,而是在认清生命悲剧本质后,一种对抗虚无的积极姿态。“空对月”的“空”字,充满了对生命可能被虚度的深刻恐惧。
第四联:“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上天造就我的才干,必然有其用武之地;千金散尽,终将再度归来。
这是全诗最核心的自信宣言,亦是最深沉的自勉与反讽。“必有用”是扎根于盛唐文化血脉中的不朽信念,而“还复来”则是对世俗价值体系的彻底超越。这声呐喊,既是对外部世界的宣告,更是对内心彷徨的镇压。
第五联:“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且以烹羊宰牛来寻求欢乐,定要一气饮下三百杯!
以原始而隆重的宴饮仪式,将抽象的“欢”具体化为具有冲击力的感官盛宴。“三百杯”的夸张,意在用物质的极大丰盈来填补精神的巨大空洞。
第六联:“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岑夫子啊,丹丘生,请尽情饮酒,杯不要停!
突然插入的直呼其名,打破了诗歌的叙述节奏,将读者瞬间拉入酒宴现场,极具戏剧性与代入感。这是情绪升温的节点。
第七联:“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请让我为你们高歌一曲,也请你们为我侧耳倾听。
由“饮”至“歌”,是情感的进一步升华。诗人不仅要畅饮,更要呐喊,标志着宴饮从感官放纵转向精神宣泄。
第八联:“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钟鸣鼎食的富贵生活并不值得珍视,只愿长久沉醉,不再醒来。
这是对主流价值体系的公开决裂。“长醉不复醒”是全诗的诗眼,醉,是为了对抗“醒”时所见的现实之丑;不愿醒,是因为醒来后的世界不值得面对。
第九联:“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自古以来的圣贤皆寂寞无闻,只有纵情饮酒者能留下美名。
以惊世骇俗的历史观,完成对自身价值的重新确认。这是愤极之语,是以“饮者”的“有名”来反讽“圣贤”的“寂寞”,为自身的“失败”寻找光荣的借口。
第十联:“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昔日的陈王曹植在平乐观设宴,一斗酒值十千钱,纵情欢笑戏谑。
借曹植这位才高八斗却备受猜忌的古人以自况。曹植的“恣欢谑”背后是政治失意的悲凉,李白在此找到了跨越时空的知己,使个人的悲愤获得了历史的纵深。
第十一联:“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主人为何要说钱不够?只管去买酒来,我与你们对饮。
此句将诗人的反客为主与豪迈性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其情感已达到忘乎所以的巅峰状态。
第十二联:“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那名贵的五花马,价值千金的皮裘,叫孩儿们统统拿去换来美酒,与你们一同消解这万古之愁!
结尾达到全诗情感的沸点。“万古愁”三字,石破天惊。它点明诗中之愁,并非一己之得失,而是对生命短暂、怀才不遇、志业成空等人类永恒困境的深刻悲悯。以物质上的极致挥霍,来对抗精神上的终极困境,构成了一个无比悲壮而又绚烂的悖论。
整体赏析:
这首作品是一部交织着极度自信与极度绝望、狂欢与悲怆的复调交响乐。它的情感结构并非线性上升,而是“悲—欢—愤—狂”的循环激荡。诗歌以“黄河”的宇宙意象始,以“万古愁”的哲学慨叹终,构建了一个从空间到时间、从个人到历史的宏大框架。在这场语言的狂欢中,李白将“酒”这一物象提升为生命哲学的核心象征:它既是麻醉剂,也是催化劑;是逃避所,也是斗爭场。全诗以其排山倒海的气势、惊世骇俗的语言和深刻的生命悲剧意识,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撼人心魄的“醉中独醒”之作。
写作特点:
- 情感的雷霆节奏与复合张力:诗歌情感大起大落,如黄河波涛,奔涌跌宕。自信与自卑、欢乐与悲愤、旷达与激愤等多种矛盾情绪交织并置,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
- 夸张的极限化运用:诗中夸张无处不在,从“三百杯”到“万古愁”,均以极限化的数字与概念挑战读者的想象边界,服务于其喷薄的情感表达。
- 句式与韵律的自由奔突:杂言句式长短错落,节奏急促变幻,如“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完全打破了诗歌的常规节奏,模拟了酒酣耳热时的语言状态。
- 自我形象的史诗性塑造:诗人通过这首诗,成功地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谪仙人”——盛唐的“酒神”形象,这个形象远远超越了其本人,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
启示:
这首诗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在绝境中依然保持生命强力的悲剧性英雄主义。它告诉我们,当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无法解决时,人可以转向内心,以精神的极度张扬来确证自身的存在价值。李白的“醉”,是一种清醒的沉沦,是以表面的放纵来完成内在的坚守。在当代社会,我们或许不再有“千金散尽”的豪情,但依然会面临各种“万古愁”的现代变体——意义的虚无、成功的焦虑、时间的压迫。这首诗启示我们,真正的强大,或许不在于消灭忧愁,而在于像李白一样,拥有将“愁”化为壮丽诗篇、将绝望升华为生命狂欢的勇气与能力。在认清人生悲剧性的底色之后,依然能喊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并为之尽情燃烧,这才是这首作品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根本原因。
关于诗人:

李白(701 - 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诗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星座之一,而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当属李白。李白将中国的古典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推向了顶峰,并以卓越的成就影响了古今中外一代代优秀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