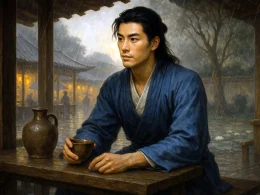「杂诗三首 · 其三」
沈佺期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
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
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
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赏析:
此诗作于武则天时期。那时国境虽盛,而边疆战事频仍,北方的黄龙戍(今吉林农安一带)年年用兵,士卒久戍不归,家室离散。沈佺期身为朝中文士,对战事的频繁与民间疾苦深有感触,于是借“闺怨”题材寄托对战争的厌倦与对和平的向往。这首诗虽题为“杂诗”,实则是一首带有强烈反战色彩的思妇诗,情真而意深,体现出诗人将个人哀怨与时代悲情融为一体的艺术自觉。
第一联:“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
听说黄龙戍那边战火连年,从未停息。
诗人以平易自然的口吻开篇,“闻道”二字仿佛闲谈,却暗含叹息;“频年不解兵”四字则将连年征战的残酷与无休止的战争状态揭示无遗。没有直接批判,却让人感到民生困苦与家国疲弊。语气平淡,情意深厚,开篇即定下全诗悲怆的基调。
第二联:“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
可怜那曾照闺中的明月,如今却长久照着汉营的军帐。
此联以“月”为线索,连接征人与思妇。诗人并不写人,而写同一轮月光在两地徘徊,用空间转换暗示情感共振。对于征夫,它是寄思的明月;对于闺人,它是寂寞的象征。一个“可怜”道尽千言,“闺里月”“汉家营”一静一动,一室一野,对比鲜明,意象含蓄。沈佺期在此以月寓情,使诗意空灵而深婉。
第三联:“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
少妇此刻春思萌动,良人昨夜依然深情难忘。
这两句工对精严而极具巧思。“今春意”与“昨夜情”互为映照,春夜对比、今昔交织,情感在时间的错位中延展。少妇的“春意”是对良人的思念;良人的“昨夜情”是对妻子的回忆。诗人以互文手法写出思妇与征夫心灵的同频共鸣,短短十字,却展现出一对分离夫妻隔空相恋的深情与惆怅。
第四联:“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谁能举起旌旗战鼓,一举攻取敌城,使战争早日结束?
结尾转为慨叹。由私情升华为公愿,既是思妇与征夫的心声,也是诗人本人的呼喊。诗人以“问句”作结,既似祈盼,又含无奈,语势顿挫中见沉痛。它回应首联“频年不解兵”,形成首尾照应,使全诗收束有力。
整体赏析:
整首诗以闺怨为表,以反战为里,通过“月”与“情”两条线索,将离思与战争相互交织。诗中既有闺中少妇的哀思,也有征夫思乡的无奈,更有诗人对久战不息、民生困苦的隐忧。
从艺术手法上看,诗人摒弃了宫体诗的艳丽铺陈,以平淡自然的语言描摹最普遍的人间情感。诗中“今春意”“昨夜情”是全篇情感的核心,极富音乐性与节奏美,体现沈佺期在格律之外追求真情的突破。最后以设问收尾,不仅余音袅袅,更透露出一种无力的呐喊——这不只是少妇的悲歌,更是整个乱世的叹息。
写作特点:
- 以小见大、情中寓政:借闺怨抒反战,体现人道主义关怀。
- 以“月”为媒、双向抒情:共月而思,构成跨时空的情感共鸣。
- 语言自然、含蓄深远:平语入诗,情真意切而无雕饰。
- 结构对称、声律和谐:颔联与颈联对仗精工,节奏流畅。
- 结尾含思、情境双转:以问句收篇,留白广阔,兼具反思与哀叹。
启示:
诗人以一个女子的细腻情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战争创痛,以个人的相思写尽人间离苦。这首诗启示我们:真正的同情并非来自宏论,而来自对个体生命的怜悯。沈佺期通过“闺里月”的温柔与“旗鼓”的沉重形成强烈反差,揭示了战争背后最深沉的悲哀——它摧毁的不仅是城池,更是情感与人心。诗人以柔婉笔触写出沉痛主题,使这首诗超越了宫廷赞颂的狭隘,成为早唐最具人文光彩的篇章之一。
关于诗人:

沈佺期(约656 - 715),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初唐重要诗人。上元二年进士,历官通事舍人、给事中,后因依附张易之被流放驩州,遇赦后迁台州录事参军。他与宋之问齐名,并称“沈宋”,二人对唐代五言律诗的定型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其诗多应制奉和与羁旅抒怀之作,风格精丽严整,尤擅七律,《全唐诗》存其诗三卷。代表作《独不见》“卢家少妇郁金堂”被誉为初唐七律的典范,《夜宿七盘岭》则展现流放途中的清峻诗风。沈佺期的创作标志着六朝余韵向盛唐气象的过渡,在近体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