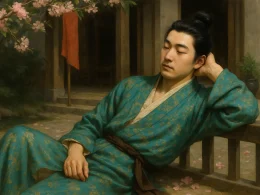「西河 · 金陵怀古」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
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
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
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
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
周邦彦
想依稀、王谢邻里。
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
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赏析:
这首词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间,彼时北宋王朝内忧外患,南有方腊起义,北有金兵虎视,国家风雨飘摇。周邦彦因公差往来江南,曾途经金陵(今南京),登高凭吊旧迹,触景生情,遂写下此作。这首作品正是在这种国势将倾、个人飘泊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词中通过层层景物描写,寄托对南朝遗迹的追忆、对人事兴亡的感慨,展现周邦彦词风中少见的雄浑苍凉与家国之思。
第一段:“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
这块风光绮丽的土地,南朝当年的盛况还有谁记得?群山环抱旧都,清江蜿蜒流绕,山峰对峙如美人发髻般绵延。如今江潮寂寞拍打着孤城,远远风帆穿过天际。
本段以“佳丽地”发端,赞美金陵山川之秀丽,紧接“南朝盛事谁记”转出怀古之情,意在哀叹昔日辉煌湮没不闻。山水形胜描绘精致,尤以“髻鬟对起”形容山峦之美,极富想象力。而“怒涛寂寞打孤城”,由景入情,以冷寂江声反衬城市荒凉,传达出人去楼空、时代衰败的悲凉情绪。
第二段:“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
断崖上的老树仍歪斜着倚在山石间,仿佛当年莫愁女的船曾拴系于此。只剩下一片青苍旧迹,浓雾掩映,连城墙残垒也模糊难辨。夜已深,月光悄悄掠过女墙,我伫立东望淮水,满怀悲伤。
本段转入对古迹的观望,景物静中有动。“断崖树”“雾沉半垒”皆为物是人非的象征,而“莫愁艇子”则引古入今,带出金陵传说。末句“月过女墙”“伤心东望”,写景极致之后突然一笔情感透出,点明词人登临之处、夜观之时,衔接上下段,并把情绪导入深层哀思。
第三段:“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酒幌飘扬、鼓乐喧闹的热闹街市如今在哪?仿佛还能模糊辨认出,那儿正是昔日王谢两家比邻的所在。燕子不知人间历经多少代更替,依旧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巷弄。看那成双成对的燕子,在夕阳中似乎也在诉说着兴亡往事。
最后一段由目下热闹景象转入历史沉思。“王谢邻里”指的是曾经显赫的家族,如今只剩模糊印象。“燕子不知何世”,一句平淡却深沉,以小物见沧桑。词人赋予燕子以人的情感,似与其对望、感怀今昔。这种托物寄情的结尾方式,极富感染力。“斜阳里”收笔,更添一层苍凉与历史沉沉的叹息。
整体赏析: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史怀古之作,也是周邦彦词中风格最为沉郁雄放的一篇。词人以金陵(建康)为时空背景,通过“山川清丽”与“古迹残破”的强烈对比,引出南朝旧事的湮没、盛世浮华的消散。词的三段布局疏密结合:首段写大景,突出山川之雄;中段写中近景,强调历史痕迹;末段由眼前市景及燕子引发兴亡之思,将空间、时间、人事三者融为一体。尤其“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将物我对照、人事代谢之感推至高潮,诗意沉厚,余韵无穷。
写作特点:
- 分段递进,层层展开:从山水形胜到旧迹残影,再到市井人家,空间层层推进,情感愈加深沉。
- 以景衬情,寓情于物:全词无一处直抒胸臆,却处处饱含兴亡之感,如“怒涛寂寞”“雾沉半垒”“燕子入巷”,景语即情语。
- 化用典故,自然精炼:“莫愁艇子”来自古乐府,“王谢邻里”指涉门第显赫,自然融入,不显堆砌。
- 语言兼具雄壮与婉约:开篇有势,结尾有情,既有金陵旧都的雄浑恢宏,又有燕语斜阳的细腻幽情,体现周邦彦词艺的双重张力。
启示:
真正动人的抒情,并非靠直白诉说,而在于借景寄情、以物兴感。无论是怒涛拍岸的孤城,还是呢喃低语的燕子,皆被词人赋予了情感与思想,构成了一部没有议论的“历史”,一幅浓缩时光的长卷。这种怀古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缅怀,更是一种对现实的警醒与反思。对于我们今日而言,诗词仍能成为感知历史、理解沧桑、体悟人生的重要媒介。
关于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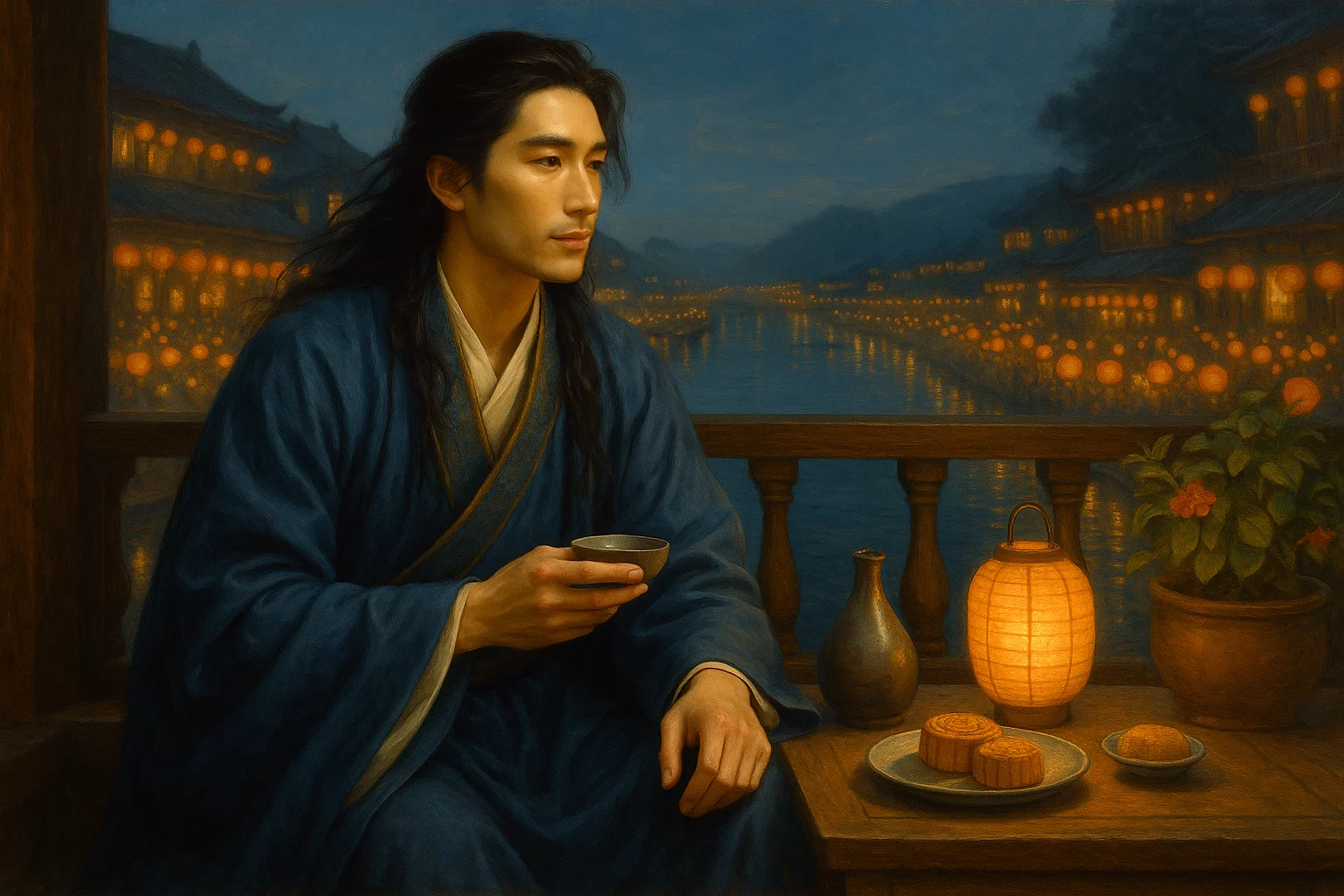
周邦彦(1056 - 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北宋婉约词集大成者。元丰初为太学生,后提举大晟府,精通音律。其词富艳精工,《清真集》存词180余首,《兰陵王·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开创"沉思前事"的铺叙手法;《苏幕遮》"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写景如画。创制新调数十种,格律严谨,被奉为"词家之冠",陈廷焯称其"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诗作《汴都赋》宏丽铺陈,曾受神宗赏识。影响南宋姜夔、吴文英等大家,为格律词派开山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