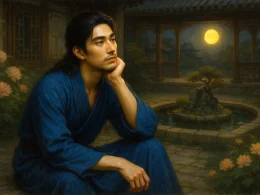「南歌子 · 驿路侵斜月」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
短篱残菊一枝黄。
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
吕本中
只言江左好风光。
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赏析:
这首词作于南宋初年。当时北宋灭亡不久,词人吕本中随宋室南渡,身处江左(今江南)之地,却心系沦陷的中原。重阳佳节之际,他途经乱山深处,旅途孤寂、故园难归,触景生情,于是写下此词。这不仅是对眼前景物的描绘,更是对国家沦亡、个人命运沉浮的深切感怀,展现出一位南渡词人浓重的家国情怀与身世之悲。
上阕:“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
天色微明,我已踏上旅程。驿路在斜挂的残月下隐约可见,脚下的小桥尚积着一层清寒的晨霜。路旁一处村舍边,低矮篱笆围起的小园中,菊花已是残败,仅余一枝微黄。此时正值重阳佳节,我却在这群山环绕、人烟稀少的地方独自度过。
这一阕从“驿路”开笔,写早行途中所见。斜月之下的驿路和晨霜覆盖的溪桥,是冷寂之景,也暗寓旅人孤寒的身世。词人用极简笔法刻画出一个“早行客”的画面,却蕴含深深的飘泊之感。接着,以“短篱残菊”点明时令已至深秋,重阳节本该登高望远、饮酒赏菊,如今却只见荒篱之下,一枝孤黄。视觉上的凋敝与节令上的对比,更添凄凉。
尤其最后一句“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一语双关。“乱山深处”既是实景,又象征身世——宋室南渡、山河破碎之际,词人竟在这样的背景中孤行过节,这种“过”不只是时间流逝的客观叙述,更是心灵无处安放的无奈体认。一个“正是”,道尽落寞,一句“五字”,胜过千言。
下阕:“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寄宿在旅途中,心绪纷扰辗转反侧,自然是无梦可依。夜晚愈发寒凉,时光似乎也格外漫长。人们常说江左的风景极好,却不知我在这好风光中,每每思念中原故土,心中愈发凄楚难安。
下阕转入夜间情境,由“早行”变“夜宿”,从视觉的“霜月残菊”进入听觉与心理的“寒更无梦”。“旅枕元无梦”不仅描写失眠的生理状态,更是心有所思、思绪难安的心理写照。“寒更每自长”用“每”字强调这并非偶发,而是旅途中屡屡重现的煎熬,这样的夜晚一再延长了词人的乡愁与寂寞。
三四句转而抒发深层情感:表面看来,江南风光旖旎,是人们艳羡之地;但对一位来自北地、心怀故国的士人而言,这片美景反成异乡之证。世人只道江左风光好,却不知这“好风光”掩盖的是他日夜思念故土的内心苦楚。正因为“不得归”,才使得“归思”愈发撕心裂肺。末句“转凄凉”不仅是情感的陡然逆转,也是全词主旨的集中点——身在“好风光”中,却心藏“故国恨”,这正是南渡文人的内在创伤与精神现实。
整体赏析:
全词以“旅途所见”起笔,由景入情,上阕写早行见闻与重阳节景,下阕则由夜宿之寂转入中原难归的沉痛感怀。看似是一首羁旅词,实则寄寓着亡国之痛与思归之恨。词人以清冷的斜月、晓霜、残菊、乱山等意象构建出一种凄清寂寥的氛围,而内心情绪则在节令触发、夜梦难成、思乡难归的层层推进中,愈发沉郁哀婉。全词情深而不露,感伤而不怨,既有画面感,又富含思想深度。
写作特点:
- 景中含情,以景引情:词人没有直接抒发感情,而是通过斜月晓霜、篱菊残黄等景象传递内心的孤独与凄凉,做到情景交融。
- 节令铺垫,感情推进:借重阳节作为感情转折点,将羁旅之苦与家国沦陷相连,情感从思亲、思乡推展到思国,层层递进。
- 用典精炼,意蕴深远:“江左好风光”与“中原归思转凄凉”的对比,点出“身在江南、心在故土”的内心矛盾,极具南渡士人特有的感伤格调。
- 结构紧密,语淡情深:短短小令,却章法井然,情感隐忍含蓄,形成了吕本中词作独有的“词浅意深”的艺术风格。
启示:
这首词让我们看到,真正动人的作品往往并不需要直白喊痛,而是借助节令、风物、旅情等意象,细腻地表达深沉的情感。吕本中在《南歌子》中,以清新之笔写沉痛之情,不仅表现出南渡文人对中原的深切怀念,也传达出一种“不忘本”的文化精神。在今天,我们仍能从中体会到对故乡、亲人、文化归属的共鸣,理解那种“人在江南心在北”的精神裂痕与文化坚持。
关于诗人:

吕本中(1084 - 1145),字居仁,号紫微,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南宋著名诗人和理学家。作为江西诗派的重要理论家,他提出"活法"说,主张在遵循法度的基础上追求自然变化。其诗作《东莱诗集》存诗1270余首,《春日即事》"病起多情白日迟"展现圆融自然的风格,《兵乱后杂诗》则真实记录了靖康之变的时代苦难。所编《江西诗社宗派图》首推黄庭坚为宗,对宋代诗学理论影响深远。刘克庄评其诗"流转圆美如弹丸",在江西诗派向中兴四大家过渡中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