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楼和张仲素 · 其三」
白居易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
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赏析:
这首其三作为组诗的终章,白居易的笔触从楼内孤影(其一)、箱中遗衣(其二),转向了楼外更辽阔的时空——生死之界。诗人在此不再满足于纯粹的“代言”与心理摹写,而是引入外部叙事者(客),以冷静到近乎残忍的客观物象对比,对关盼盼的生存状态发出直抵存在本质的诘问,将个人的悲剧命运置于草木无情、天道永恒的宏大背景下审视,使组诗的思想境界跃升至哲理性高度。
首联: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
今年春天,有客人从洛阳归来,说他曾到张愔尚书的墓前祭扫过。
开篇以平淡的叙事口吻,引入一个关键的中间视角——“客”。这个“客”是连接生者世界(诗人、盼盼)与死者世界(张愔)的信使,也是客观事实的见证者。“今春”点明时间的当下性,“洛阳回”暗示空间的遥远与信息的迟来。“曾到尚书墓上来”,将读者的视线瞬间从燕子楼牵引至北邙山,从生者的幽居引向死者的长眠。这一句看似简单的转述,实则为下联石破天惊的对比铺设了冷静的叙事基础,也使全诗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感的客观观察距离。
尾联: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听他说,墓旁的白杨树已长得粗壮堪作梁柱;这样说来,教那楼中的红颜佳人,如何能不化为尘灰呢?
此联是全诗的灵魂,以自然物的“生”与人的“逝”构成无情而深刻的对照。“见说”承上,强调是客人的客观陈述。“白杨堪作柱”:白杨是墓地常见树木,其速生、挺拔的特性在此被赋予时间维度——“堪作柱”意味着树木在死者埋葬后的十余年间,不仅未随人亡而枯,反而茁壮成长,近乎荒谬地彰显着自然的蓬勃与冷漠的永恒。与此相对的是“红粉”(代指关盼盼)。“争教……不成灰?”是一声混合着惊叹、质问与悲悯的终极叹息。诗人运用了“以木之生,问人之灭”的残酷逻辑:连墓边的树木都在不断生长、近乎有用(作柱),那么,被遗留在世、在无望思念中消耗生命的活人,她的美貌、青春、情感与生命,怎么可能不随着时间凋零、腐朽、最终化为灰烬?这里的“灰”,既是物理的消亡,也是精神热情熄灭后的死寂。
整体赏析:
这首诗在组诗中扮演着 “结论”与“升华” 的角色。其一写 “夜长”,其二写 “箱空”,其三则直指 “成灰”——这是情感孤寂、生命荒芜之后必然的终极归宿。白居易通过“客”的视角与白杨的意象,完成了一次叙述策略的巧妙转换:从内视(盼盼的感知)转向外察(他者的见证),从情感渲染转向事实陈述,从心理时间(“一人长”)转向物理时间(树木生长)。这种转换带来的是一种更为清醒、也更为残酷的认知:在永恒运转、漠然生生的自然法则面前,个人的忠贞、思念、乃至整个悲伤的生存状态,都面临着被质疑、被解构的可能。白杨的“堪作柱”与红粉的“成灰”,不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存在境遇的赤裸对照,逼迫读者思考:当思念的对象已归于尘土,且连其墓木都已欣欣向荣时,生者以全部生命守护的“过去”,其价值与意义究竟何在?
写作特点:
- 叙述视角的介入与间离效果:引入“客”这一第三方叙述者,使诗歌从纯粹的主观抒情,转变为包含“传闻-转述-感慨”的多层叙事结构,增强了事件的真实感与感慨的客观性,也制造了冷静的审美间离。
- 意象对比的极端性与哲理性:“白杨”与“红粉”的对比,超越了常见的“松柏-红颜”的脆弱性比喻。白杨的“堪作柱”是积极、有用、生长的意象;红粉的“成灰”是消极、无用、消亡的意象。这一对比不仅关乎时间,更关乎存在价值在自然法则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巨大落差,充满哲学张力。
- 反问句的震撼力与开放性:“争教红粉不成灰?”以反问代替断言,语气更强烈,意蕴更复杂。它既是无奈的承认(终将成灰),也是不甘的诘问(何以至此),更是对命运荒谬性的深沉洞察。答案悬置,留给读者无尽的思索。
- 组诗结构的递进与收官:此诗作为组诗结尾,在意象上从“霜月”(其一)、“罗衫”(其二)到“白杨”,空间上从楼内、箱中到墓外,时间上从秋夜、十一年到树木成材,情感上从孤寂、挣扎到直面消亡,构成了一个层层推进、终至穹顶的完整艺术建筑。
启示:
这首诗将个人的悲剧,置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欧阳修语)的永恒矛盾中审视。它揭示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困境:人类的情感执着(如盼盼的守节),在面对冷漠且持续生长的自然世界时,可能显得既崇高又荒诞,既动人又虚无。 白杨在墓旁无知无觉地成材,仿佛是对死者乃至生者情感的某种嘲弄或超越。
这首诗促使我们反思情感与时间、记忆与生命的关系。我们是否也曾为某种“过去”或“信念”而活,如同守护一件“空箱”中的“罗衫”?当外界时光流转、草木荣枯(“白杨堪作柱”),我们内心的那个世界是否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成灰”?白居易没有给出答案,但他以诗意的锋利,剖开了这一困境。
它启示我们,在珍视情感与记忆的同时,或许也需要一种对生命本身、对自然流转的更大敬畏与清醒。真正的纪念,未必是静止的守候与自我的消耗,也可能是在承认“红粉终成灰”的必然之后,依然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找到与生生不息的“白杨”世界共存、甚至对话的方式。这并非对深情的背叛,而是在更广阔的宇宙尺度下,对生命韧性另一种可能性的探寻。白居易此诗,因其深刻的悲剧性与哲思性,使得“燕子楼”的故事,最终超越了贞节烈女的单一范畴,成为关于人类存在境遇的一则永恒寓言。
关于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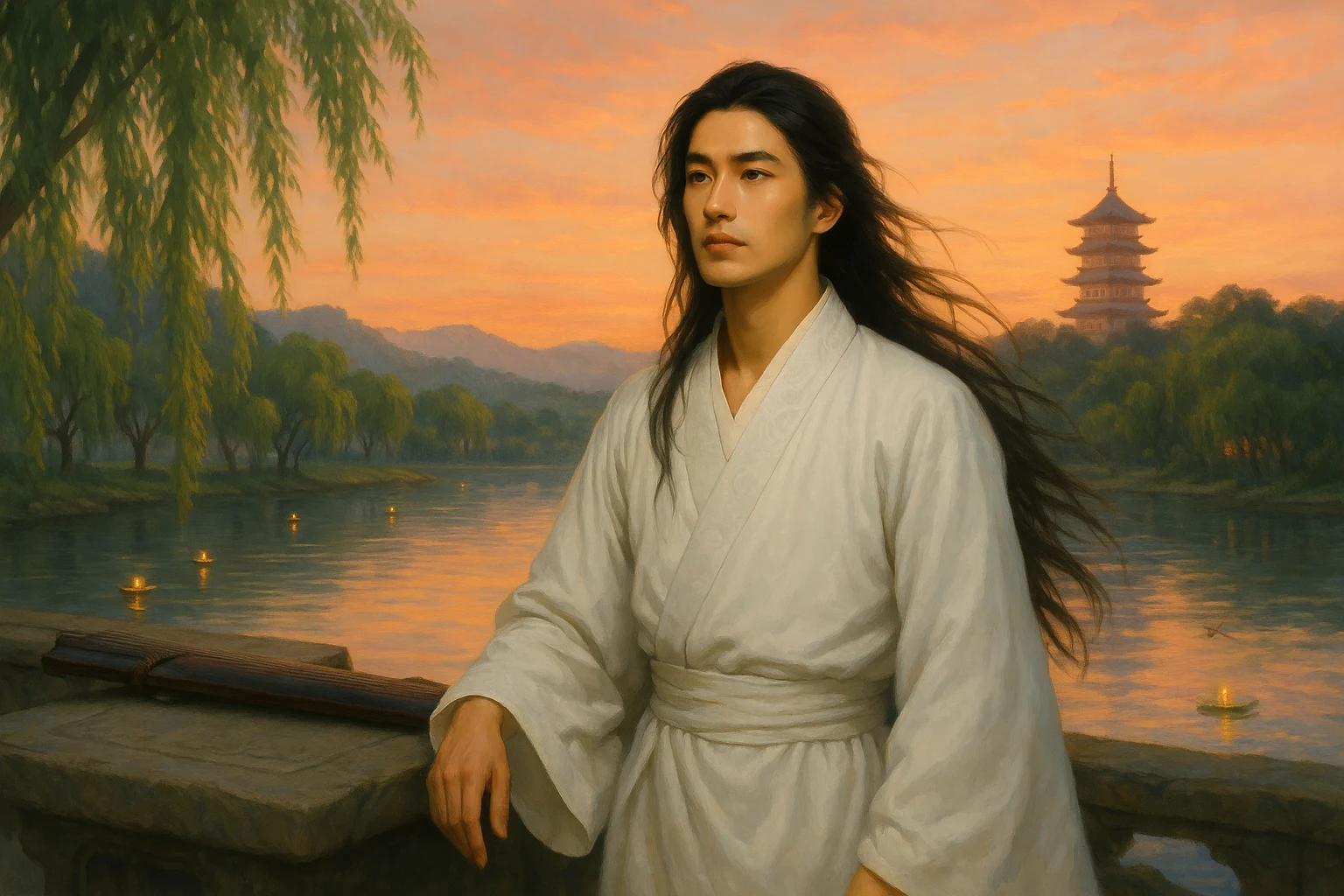
白居易(772 - 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人称白傅。原籍太原,后徙下邽(今陕西渭南)。白居易是唐代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其诗有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等类,也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