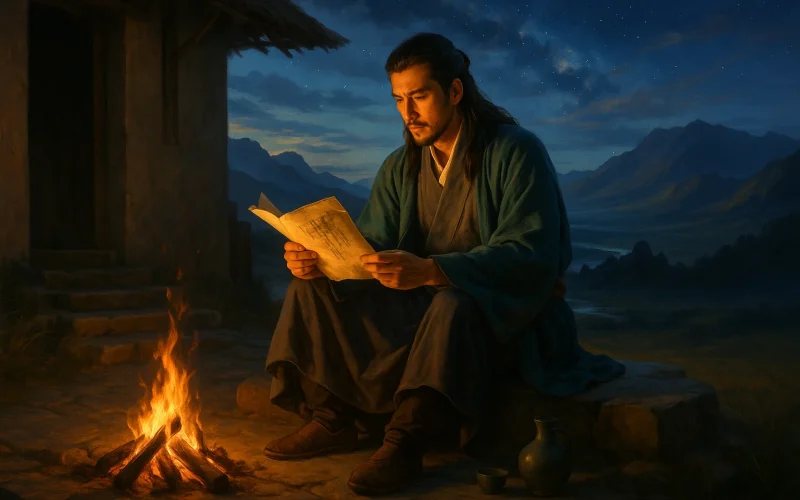「饮酒 · 其二十」
陶渊明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赏析:
这首诗作于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晚年时期,是《饮酒》组诗的最后一首,具有强烈的总结性与反思性。此时的陶渊明对时代衰败、风俗颓废感慨尤深,而自己的归隐与独醉,也愈加带有一种无奈中自持的哲思意味。他借醉酒之态抒发忧思,在深沉的文化思辨与现实批判之间,展现出士人的自省与坚守。
第一联:“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伏羲神农时代已久远,如今世人已少有淳朴真实之人。
诗人感慨人世间风俗日渐浇薄,古代那种质朴纯真的精神风貌早已不复存在,言语中透出对现实的深切忧虑。
第二联:“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孔子勤勤恳恳,致力于修复世道之淳风。
以尊崇口吻提及孔子,赞其“弥缝”乱世,试图恢复古风古道,表达对先贤精神的敬仰之情。
第三联:“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虽未见凤凰来仪,礼乐制度却一度得以更新。
象征美政的凤凰未至,但在孔子努力下,世道仍短暂呈现中兴之象,是对古代短暂清明的缅怀。
第四联:“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洙泗之音渐微,文化传承至秦而尽失。
自孔子后儒学逐渐式微,至秦而遭遇焚书坑儒之灾,诗人以文化流变映照乱世沦亡,愈加悲凉。
第五联:“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诗书有什么罪?一旦间便化作灰烬。
强烈控诉秦政焚书行为,慨叹文化典籍无辜受毁,历史之浩劫引起他深切的文化忧思。
第六联:“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那些儒者一片诚心,只为拯世匡俗。
称赞历代儒者赤诚执着,却终未能扭转社会颓风,感怀之中也有几分悲悯。
第七联:“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怎奈时风如此败坏,儒家经典竟无一人亲近。
语气一转,沉痛地指出现实中经典无人问津,道德无所依归,愤慨之情愈加明显。
第八联:“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人们整日奔波,却无一人问津治世之道。
批判世人只为名利奔走,而无人关心天下大义和精神根本,现实腐败之象跃然纸上。
第九联:“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若不痛快饮酒,岂不辜负头上的布巾(隐士身份)?
将沉醉饮酒作为对抗现实的一种方式,以布巾自喻隐者风骨,又借酒自我安慰。
第十联:“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只是遗憾言多有误,望君原谅醉中人。
结句一转,似以醉酒为托辞,实则用醉语说真话,以幽默掩饰犀利锋芒,收束得极为巧妙。
整体赏析:
此诗延续陶渊明《饮酒》系列一贯的归隐哲思,但内容上却更具历史纵深与文化批判意味。诗人从上古羲农谈起,追怀孔子立教、感叹儒道失传,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与社会风气沦丧的深深忧思。在诗中,陶渊明既怀古思贤,又愤世嫉俗,借醉酒之姿,吐露真言。他那种对礼乐诗书的尊崇,对时风颓废的悲愤,以及最终寄情于酒、借醉自慰的方式,都极具典型意义。整首诗在表面洒脱中蕴含深切的文化情怀,是对“士之大者”的温柔回响。
写作特点:
这首诗语言自然而蕴藉,极富古典意味,诗意的推进也具有强烈的历史层次感。陶渊明擅用“怀古论今”的结构,将文化沉思与个体命运交织,使得本诗既有对过往圣贤精神的礼赞,又有对当世风俗堕落的控诉,悲愤中饱含理性与坚守。在表现手法上,诗人巧妙融合叙述、议论与自我解嘲,以“醉人”之口发出最真挚的警语,使诗意既不沉重,又足够深刻,形成一种似醉非醉、似谬实真的独特艺术风格。整首诗也恰好为《饮酒》系列作出一种哲思总结与精神归宿的表述。
启示:
这首诗启示我们,当理想与现实冲突,社会风气败坏、文化价值失落之时,真正的坚守并非消极逃避,而是如陶渊明般,以清醒的哲思与人格的独立,在“醉言”中透出深意。哪怕被时代所遗忘,一个人也可以以读书与饮酒为伴,维护精神的清白与尊严,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种隐而不退、醉而不昏的人格姿态,仍值得我们在当代反思与敬重。
关于诗人:

陶渊明(公元365年 - 427年),字元亮,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出生于江西九江附近的柴桑。他不仅在文学上开创了以田园为主题的新体裁,用平淡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人生哲理,而且他的诗文风格更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恒久的审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