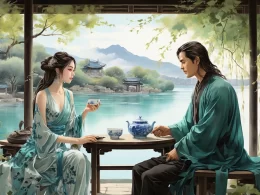「江州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
刘长卿
生涯岂料承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
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
寄身且喜沧洲近,顾影无如白发何!
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遣慎风波。
赏析:
这首诗作于公元766年左右,是刘长卿在由潘州贬移睦州途中,路过九江时写给薛六、柳八两位朋友的告别之作。当时的潘州地处岭南边远荒蛮之地,环境恶劣;而睦州虽也临海,却属东南富庶之区,相较之下已是一种“幸中之幸”。因此,诗人此番迁转虽然仍带贬意,但较之前的谪居之地有所改善,也让他略感欣慰。在这悲喜交错的情感中,刘长卿写下了此诗,既表达对现实的感慨,也流露出对朋友深切的感激。
第一联:“生涯岂料承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
我一生漂泊潦倒,哪曾料想会受到皇恩;世事虚浮,我早已学会借酒浇愁、醉里高歌。
这一联以自嘲的反语开篇,“承优诏”本应是荣耀之事,但放在诗人早已参透宦海沉浮的心境中,却显出一种讽刺的意味,表现出对命运无常的冷峻认知与身世飘零的愤激情绪。
第二联:“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
江上明月高悬,胡地归雁掠空而过;淮南秋意渐深,树木凋零,楚地青山重重叠叠。
此联转入实景描写,描绘出九江一带秋夜的凄清画面。归雁、明月、落木、楚山,皆是传统送别诗中的意象,也传达出诗人内心的清冷、孤寂和漂泊感,寄托着贬谪路上的悲愁情绪。
第三联:“寄身且喜沧洲近,顾影无如白发何!”
如今虽贬迁异地,但还能寄身于靠近沧海之地,也算一喜;只是回望镜中白发,实在无可奈何。
这两句情绪由凄苦转为稍感欣慰,“沧洲近”暗示睦州虽偏,但自然环境尚可,“寄身”二字表现出苟全之意。然而紧接着的“白发”,又将读者拉回到衰老与人生无力的现实中,感伤中带着一点豁达。
第四联:“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遣慎风波。”
如今我年迈体衰,行动蹒跚,早已与世浮沉;却仍愧对你们一再叮咛,要我慎防仕途风波。
最后一联语气婉转深沉,将朋友薛六、柳八的临别嘱托化为深刻的感动。诗人以“龙钟”自状,透露出迟暮无奈,而对朋友的关怀用“愧”字回应,情真意切。
整体赏析:
整首诗以深沉感慨为主线,将个人遭遇与时代背景交融。开篇即以反语展示对命运的讽刺与无力,接着通过秋夜江景的写意,寄托愁绪;中段转为哲理性的自我安慰与对身世的审视,末尾回归现实中的友情,点明诗题“赠别”之义。
刘长卿在这首诗中既不沉溺于哀伤,也不妄作高歌,而是以冷静笔调抒写现实的悲凉与人情的温暖。他以“沧洲近”聊以自慰,以“愧君言”表现知己之情,全诗情感层次丰富,从身世飘零到友情惦念,节奏沉稳,动人心弦。
写作特点:
- 反语入诗,冷峻自省:“岂料承优诏”看似感恩,实则讽刺,体现诗人洞察世态的深刻目光。
- 景中藏情,寓意深远:江月、归雁、木落等意象,皆为传达心境服务,景语与情语交织。
- 情绪起伏,结构明晰:悲—喜—忧—感,层层递进,宛如心绪的四重奏。
- 以情结尾,温婉收束:诗末回到现实,用“愧君”点出友情,柔化整首诗的沉重色彩。
启示:
这首诗启示我们,在人生起伏与仕途沉浮之中,最可贵的或许并非荣耀的官职或命运的转机,而是对自我命运的清醒认知,以及在困顿中依然不忘的友情与惦念。诗人身处贬谪,仍能感知“沧洲近”的一线之喜,对朋友深情叮嘱的一句“愧君”,更显人间情义的珍贵。这是一种在风波中历练出的豁达,也是一种经历人世后沉静而温厚的智慧。
关于诗人:

刘长卿(?-约786),字文房,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少时读书嵩山中,后移家鄱阳(今江西),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进士及第。他的诗也属于王、孟一派,五言诗最著名,也最为自负,曾自以为“五言长城”,即是无人能超越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