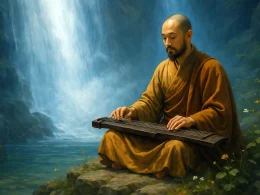「省试湘灵鼓瑟」
钱起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是钱起参加省试时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不仅一举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也成为省试诗中的传世佳作。省试是唐代进士科考试的重要环节之一,通常由礼部侍郎主持,应试者需依题作诗,多为五言律诗,要求用韵工整、内容贴题。此诗题取自《楚辞·远游》中“使湘灵鼓瑟兮”,典出舜帝妃子化为湘水女神的传说,整首诗围绕湘灵鼓瑟这一虚幻意象展开,哀艳凄婉,动人心魄。
第一联:“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湘水女神擅长演奏云和之瑟,我常听闻她乃舜帝之妃,神灵飘渺。
此联开篇点题,直入湘灵传说。“云和瑟”是古代传说中的瑟名,象征精美、神圣的乐器,其“云和”亦可引申为虚渺、缥缈的声音意象,极具仙灵之气。“帝子灵”暗合《楚辞》中舜妃化为湘水女神之说,将人神交融的湘灵形象带入抒情场域。诗人以此奠定全诗神话色彩的基调,使湘灵既是传说中的人物,又是情思的象征载体。
第二联:“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水神冯夷随曲而舞却徒具形式,真正感伤的却是那些身世飘零的楚地游子。
“冯夷”是中国古代水神之一,常与江河湖海相连,这里象征天地之间的无知旁观者。“空自舞”传达出一种与乐曲情绪不合的疏离感,而“楚客”一词则将诗人代入其中,强化贬谪失意者对瑟音中悲意的共鸣。通过对比,突显情感真正的知音并非神祇,而是凡间有共苦之感的游子,从而引发更深的感伤。
第三联:“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这哀婉的曲调竟能令金石为之动情,那清越之声甚至穿透幽冥。
本联描写琴音的力度与深度。“金石”象征坚硬、无情之物,而“凄金石”则是说连这般刚硬之物也被琴音打动,夸张中寓真情。接着“清音入杳冥”则将听觉推入空间层次之深远,幽冥不仅是死者之境,亦象征心灵深处的潜意识与极致孤寂。音之所至,情之所感,可通生死、可动天地,是传统“感物动情”美学的极致体现。
第四联:“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舜帝在遥远的苍梧之地也因曲而动情,山间白芷草亦被琴音感动,散发出清香。
此联以拟人化和自然通感手法,将湘灵之思的感染力扩展到神明与草木之间。“苍梧”乃舜崩逝之所,“怨慕”将舜对湘灵的追念之情拟想具象化,增加诗意的深沉与广阔。“白芷”本为香草,常见于《楚辞》,象征高洁情操和哀思情意。“动芳馨”将无声的香草赋予感情回应,使神灵、人、物三位一体,构成楚辞传统中的“哀感天地”氛围。
第五联:“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
哀曲随湘水之流传至潇浦,更化为凄厉之风掠过洞庭湖面。
本联以空间延展推动情感高潮。“流水”与“悲风”是极富楚地诗意的意象,既是自然之物,亦是情思流转的外化。“潇浦”“洞庭”均为湘灵传说的重要背景地,层层推进,使湘灵之音由个人私情升华为天地共感之大哀。“传”“过”两个动词强化了琴音的流动性,也象征湘灵的哀思如水无尽,飘荡四野,弥漫整个楚地。
第六联:“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乐曲终了,湘灵不见了踪影,唯有江上的青山巍然不动,静静伫立。
结尾以景收情,将神秘的湘灵虚化于自然。“人不见”既点出湘灵形象的飘渺难留,也暗寓人生如梦、知音难再的哲思。“数峰青”不仅是一幅静美画面,更具有象征意味:青山常在,而知音难寻,情感终归于山水,形成了“以景结情、情中藏思”的艺术手法。虚实交错,余韵无穷,点明全诗“曲终情未了”的美学核心。
整体赏析:
整首诗结构严谨,情感充沛,既承载了传统楚辞的神话意蕴,又以唐人独特的笔法加以重构。诗人由湘灵鼓瑟切入,通过听觉感受展开丰富的想象,融合神话人物与自然景象,将哀思与艺术美感紧密结合。其用典自然,语言典雅清丽,感情内敛却不失深沉。尤其结尾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以极简之笔,转虚为实、寓情于景,既回环照应,又留有悠远的回味,被后世誉为“神来之笔”。
写作特点:
本诗作为省试应题诗,紧扣题意而不落俗套,典故运用巧妙,语言哀婉精工。钱起在形式受限的条件下,发挥卓越的诗思与艺术技巧,将神话意象与诗人情思完美融合,达到了“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境界。其写作中极重声情相通,尤擅以意境营造深沉的美学氛围,呈现出唐人律诗高远清逸的风貌。
启示:
这首诗不仅展示了钱起过人的艺术才情,也启示我们:在题材受限、格式严格的写作中,依然可以通过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佳作。湘灵鼓瑟的传说赋予诗歌以神秘与美感,而诗人通过对乐声的拟写与环境的渲染,使这段哀怨与美丽的神话充满生命力,也让我们体会到文学创作中“情景交融”“以景结情”的极致魅力。
关于诗人:

钱起(约722 - 780),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中唐“大历十才子”之首。天宝十载(751年)进士,历官考功郎中、翰林学士。其诗承王维余韵,以五律见长,《全唐诗》存其诗530余首,诗风清空雅致,严羽称其“体制新奇,理致清赡”,但部分作品流于雕琢,反映大历诗风从盛唐自然向工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