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和歌辞 · 婕妤怨」
刘方平
夕殿别君王,宫深月似霜。
人愁在长信,萤出向昭阳。
露裛红兰死,秋凋碧树伤。
惟当合欢扇,从此箧中藏。
赏析:
《相和歌辞》是汉魏六朝以来的重要乐府旧题,往往用来抒写宫怨之情。刘方平生活在唐代宗至德、广德年间,彼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宫廷与士人世界皆弥漫着压抑与无奈。这首诗承袭“宫怨诗”的传统,以代言体写一位失宠的宫人自叙离愁。所谓“婕妤”,原是汉代后妃品秩名,唐人常以之代指幽怨而不得志的宫妃。借用婕妤之口,诗人不仅描绘了冷清宫廷中的寂寞哀怨,也折射出唐代士人自身怀才不遇、幽愤难伸的处境。
第一联:“夕殿别君王,宫深月似霜。”
傍晚时分,美人在宫殿中与君王分别,幽深的宫室里只有一轮清冷的月亮,像霜一样冰寒。
这两句起笔点明“怨”的根源:失宠与别离。一个“夕”字,暗示时光将晚,象征美人恩宠已衰;“宫深”写出了环境的冷清与压抑;“月似霜”则把空间氛围推向极致冷冽。月光清白,本是美景,但与孤独的宫人相对,就成了冷落与孤寂的象征。写景中寓情,把内心的悲凉巧妙投射到月光之上。
第二联:“人愁在长信,萤出向昭阳。”
愁苦的美人被冷落在长信宫中,只能遥想那飞向昭阳殿的萤火虫,似乎代替她传递相思。
这一联承用典故。长信宫,汉成帝时冷落许皇后所居之地,历来是“失宠幽居”的象征;昭阳殿,则是赵飞燕受宠之所。诗人借“长信—昭阳”的对照,写出了美人失宠后的孤立处境。尤其“萤出向昭阳”一笔,极富象征意味:渺小的萤火,光微而不自量力,仿佛是美人无声的思念,徒然追逐帝王的宠幸,却注定无法抵达。这里通过小景衬托,含蓄而深刻地表现了失宠女子的孤寂与哀愁。
第三联:“露裛红兰死,秋凋碧树伤。”
露水浸湿了娇艳的红兰,使它枯萎凋谢;秋风吹打碧树,也让人心生凄凉与悲伤。
此联以自然景象映照人物心境。“红兰”本喻美人,鲜艳娇美,却因露水侵袭而早亡,正是失宠红颜的自况;“碧树”四季常青,却在秋日衰败,象征繁华已尽,美景难久。这里的“裛”“凋”两个动词极传神,既表现了自然界的衰落,又暗喻人事无常与情感的骤变。通过花木的枯损,折射出美人芳华不再、心境黯然。
第四联:“惟当合欢扇,从此箧中藏。”
只剩下一柄合欢扇,从此收进匣中,尘封不再示人。
全诗收束于“合欢扇”。合欢,本是夫妻情深、恩爱长久的象征。但如今却被收起,象征爱情与恩宠已成过往。一个“藏”字,意味无尽:情感的痕迹被迫收起,曾经的美好也只能封存在记忆中。结尾含蓄,却让全诗的怨情更加沉痛。
整体赏析:
全诗层层递进:由“别君王”的直接场景写起,转而到“长信—昭阳”的典故映衬,再以花木秋凉的景象寓情,最后以“合欢扇”作象征收束。诗人把幽居宫妃的孤寂心境写得细腻婉转、动人肺腑。
诗歌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宫怨情绪的描写,更在于寓意深远:婕妤之怨,实际寄托了诗人对世事无常、人生失意的感慨。宫廷深处的冷清,与文人仕途的落寞,是相通的。刘方平善于以小见大,通过代言体写女性幽怨,暗含自身的心境。
写作特点:
- 代言体写法,移情入景
诗人借婕妤口吻叙事,虚构之中蕴含真实情感,使读者能更深刻体会到孤寂与无奈。 - 典故映衬,意境深厚
长信、昭阳,既是宫室名,又承载厚重的历史与典故,增强了诗歌的文化意蕴。 - 情景交融,象征丰富
月似霜、兰花死、碧树伤,无一不是情境相生,景象即心境。 - 结尾含蓄,象征悠远
“合欢扇”由恩爱象征转为怨情象征,寄意深婉,收束全篇而余韵不尽。
启示:
这不仅是一首宫怨诗,更是一首关于人世无常与情感幻灭的寓言。它提醒世人:荣宠如月光,清冷易逝;恩爱如兰花,繁华亦将凋零。面对人事变迁,唯一能持久的,是心中的坚守与自持。对今日的读者而言,这首诗让我们明白——纵使身处孤寂与冷落,仍需学会自我安慰与自我成全,不必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外物或他人。
关于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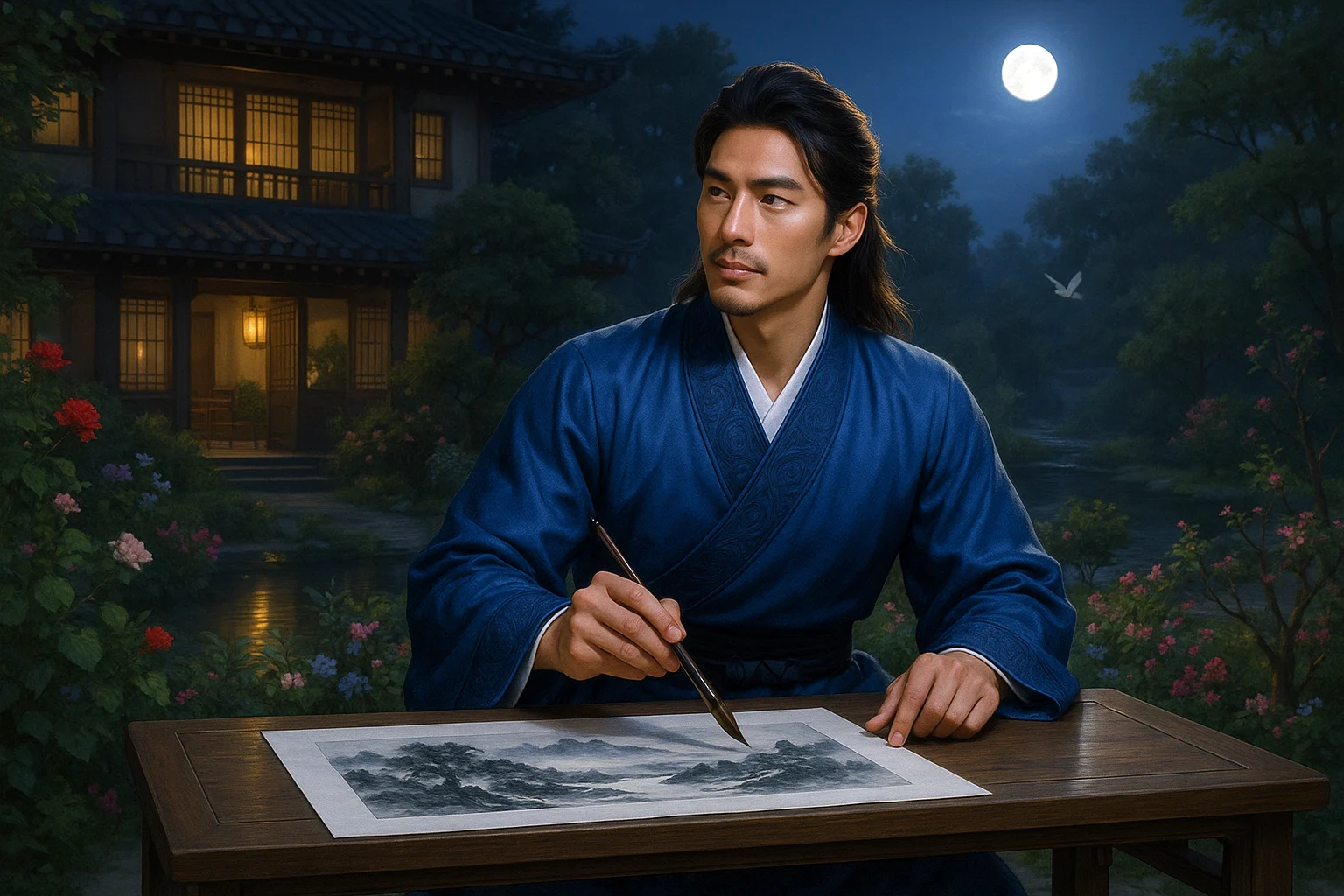
刘方平(约742 - 约785),字方平,河南洛阳人。盛唐至中唐之际的隐逸诗人、画家,以其清丽婉约、善写闺怨与月夜的诗风独树一帜。虽存诗仅二十六首于《全唐诗》,却凭《月夜》《春怨》等作跻身唐诗经典殿堂,被誉为“盛唐之清音,中唐之先声”。其诗融齐梁清丽与禅宗空寂于一炉,对后世婉约词风及日本王朝女流文学皆有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