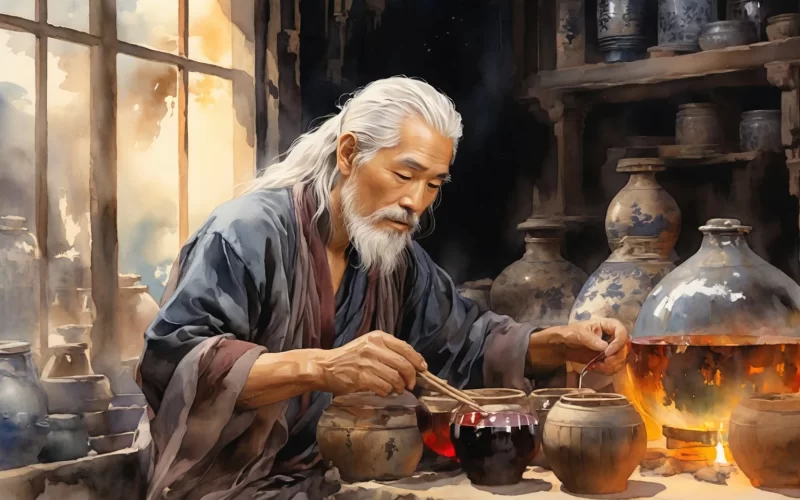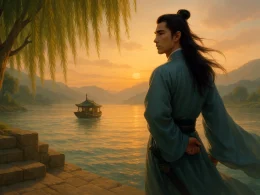「战城南」
李白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赏析:
这首诗是李白对汉乐府旧题《战城南》的再创作,但其锋芒直指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频频发动的开边战争。李白以其震撼人心的笔触,打破了传统边塞诗或豪迈或悲壮的单一色调,以近乎自然主义的残酷描写和深邃的历史洞见,对战争本身进行了彻底否定,使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具冲击力的反战宣言之一。
第一段: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去年在桑干河的源头征战,今年又转战至遥远的葱河流域。士兵们曾在条支国的海水中洗涤兵器,又曾在天山的雪原上牧放战马。这长达万里的征战啊,使得全军将士都已身心疲惫,未老先衰。
诗人以编年史般冷峻的笔调开篇,“去年”、“今年”的并置,揭示了战争的无休无止;“桑干源”、“葱河道”、“条支海”、“天山雪”这四个跨越东西南北的极端地名,勾勒出一幅幅动魄惊心的行军图,强调了战争空间的广漠与环境的严酷。“洗兵”二句,字面壮阔,内里悲凉,所谓的“壮举”是以无数士兵的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结尾“三军尽衰老”一句,是这段征程的必然结果,它控诉的不仅是肉体的损耗,更是精神与希望的泯灭。
第二段: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匈奴人将杀戮当作耕作一样平常,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上能见到的,只有森森白骨点缀着茫茫黄沙。秦朝修筑长城用以防备胡人的地方,到了汉朝,告急的烽火依然在那里燃烧不熄。
诗人的视角从当下拉向历史纵深。他首先打破了对“蛮族”的浪漫想象,直言其生存法则的残酷,但用意并非宣扬仇恨,而是为了铺垫下句:无论攻守,代价都是“白骨黄沙田”。紧接着,他以“秦家筑城”与“汉家烽火”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意象,构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时间循环。长城这一伟大的防御工事,并未带来永久的和平,只是将冲突固化,证明了暴力与对抗的永续性。这是对战争根源的深刻反思。
第三段: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烽火燃烧不息,征战永无休止。战士在野战中搏斗至死,失去主人的战马向着天空发出凄厉的悲鸣。乌鸦和鹞鹰啄食着死者的肠肚,衔起来飞走,高挂在枯死的树枝上。士兵们的鲜血涂染了荒野草莽,而将军们最终也不过是徒劳无功。由此可知,兵器乃是天下至凶之器,唯有圣人在万不得已之时,才会动用它。
此段是全诗的高潮,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场描写。诗人以毫不避讳的笔触,呈现了地狱般的景象:战马的悲鸣是情感的撕裂,而“乌鸢啄人肠,衔飞挂枯枝”则是视觉的恐怖顶点,将战争的野蛮与非人道推到极致。在这巨大的牺牲(“士卒涂草莽”)面前,任何军事功业(“将军空尔为”)都显得虚妄而可鄙。最终,诗人引《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哲思作结,这并非简单的用典,而是对朝廷“默武”政策的直接批判——当下的战争,多少是“不得已”?这最后的议论,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整体赏析:
这篇结构严谨、感情炽烈的反战檄文,全诗遵循着“现象描绘—历史追溯—本质批判”的逻辑层层推进。从空间上的无限扩张(万里征战)到时间上的无限循环(秦汉烽火),李白构建了一个无处可逃的战争囚笼。他通过极致的视觉冲击(白骨、乌鸢)与听觉渲染(马悲鸣),不仅激发了读者的怜悯与恐惧,更旨在摧毁任何关于战争的浪漫幻想与英雄主义叙事。最终,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战争的决策者,明确指出绝大多数战争都违背了“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古训。这首诗的价值,在于其超越时代的清醒与勇气。
写作特点:
- 乐府古题的创造性转化:李白继承了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注入了更强烈的个人批判色彩和更加恢弘的艺术想象力,使旧题焕发出新的思想光辉。
- 时空交织的宏大叙事:诗歌在时空上自由穿梭,从去年的桑干到今年的葱河,从眼前的条支海到历史中的秦城汉火,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宏大悲剧舞台,揭示了战争是人类历史的顽疾。
-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骇人结合:诗中对战场惨状的描写是高度现实甚至自然主义的,但其呈现出的整体效果(如“乌鸢啄人肠”)却因其极致而带有一种骇人的、表现主义式的浪漫,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 议论与描写的无缝交融:诗歌后半段,在进行了最密集的惨状描写后,顺势引出“将军空尔为”的论断和“兵者凶器”的哲理,使得议论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基于血淋淋事实的必然结论,水到渠成,力透纸背。
启示:
这首诗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重而深刻的。它首先是对任何形式战争狂热的彻底祛魅,提醒我们警惕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个体痛苦与生命代价。其次,它揭示了历史的惯性——暴力循环的可怕与打破这一循环的艰难,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建立超越对抗的和平秩序。最后,李白所引用的“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是人类处理国际争端时应恪守的最高智慧与道德底线。它告诫我们,必须对武力持有最深刻的敬畏与最审慎的态度,任何轻启战端的行为,都是对文明本身的背叛。
关于诗人:

李白(701 - 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诗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星座之一,而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当属李白。李白将中国的古典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推向了顶峰,并以卓越的成就影响了古今中外一代代优秀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