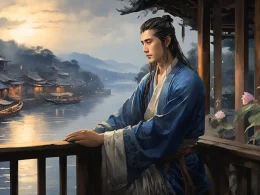「陇西行」
陈陶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代,是陈陶《陇西行》四首中的第二首。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日衰,边患不断,西北边地常年征战,士卒死于沙场者不计其数。诗人通过一则戍边将士与其妻子之间“阴阳两隔、梦里相见”的片段,寄寓对战争悲剧的深切同情,深刻揭露了战乱对千千万万个家庭所造成的创伤,是唐代边塞诗中极具反战色彩的一首名篇。
第一联:“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将士们誓言要扫平匈奴,奋不顾身,结果五千名身披貂裘的战士全都死在了胡地风沙之中。
诗人开篇即以“誓”字写出将士们出征的慷慨悲壮。“貂锦”象征军中精锐与荣誉,然而这一队身披荣耀的士兵却尽数殒命沙场。“丧胡尘”一句暗含血染黄沙、尸骨无归的惨烈景象,没有正面写战斗,却让人仿佛置身于兵戈铁马、血肉横飞的残酷战场。此联从赞美英勇入手,铺垫了下联的深情转折。
第二联:“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那些战死沙场、埋骨无定河畔的将士,仍是妻子梦中依恋的丈夫。
此联风格陡转,由雄壮转为哀婉。“可怜”道出诗人深切的同情,“无定河”则成为亡者埋骨之地的象征,而“梦里人”则代表深闺少妇内心未泯的牵挂与等待。尸骨成沙,魂梦依旧,这种极端不协调却又真实可感的对照,使整首诗的悲剧性更为深沉。她们或许至死都不知道丈夫已成白骨,而仍在梦中低语等待。这一联极具震撼力,极简之笔却画出了战争最深处的人间悲哀。
整体赏析:
诗人以对比手法构建出强烈的情感张力:一面是战士临危不惧、血洒沙场的壮烈,一面是深闺思妇不知战亡、梦中相见的柔情。正是这种“理想之壮”与“现实之哀”的落差,让读者在敬佩忠勇之余,更为战争的无情与生命的脆弱而感到震撼。诗中没有直接指责战争,却用白骨与梦境的交错隐喻,将战争带来的人伦毁灭表现得淋漓尽致,讽喻之力深远而有力。
写作特点:
此诗结构紧凑,四句两联,却完成了从激情到哀愁、从战场到闺房、从现实到梦境的转换,情境交融,意象凝练。诗人善用对比、转折、象征等艺术手法,使诗风雄浑中见柔婉,哀怨中见深情。“貂锦”与“梦里人”、“胡尘”与“无定河”这些细节设定增强了作品的象征性和艺术张力,成为边塞诗中兼具豪放与婉约的典范。
启示:
这首诗不仅是对将士英勇赴死的礼赞,更是对无数家庭破碎的哀悼。它启示我们,战争不仅吞噬生命,更留下无尽的牵挂与创伤。和平的可贵,在于它守护了人间最基本的情感纽带——亲情、爱情、家庭。而诗人的真正批判,不是对敌人,而是对战争本身,对统治者无尽征伐所带来的人道灾难。这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使这首诗穿越时代,至今仍令人动容。
关于诗人:
陈陶(生卒年不详),字嵩伯,鄱阳剑蒲(今江西)人,活动于晚唐时期。早有诗名,曾游学长安。但屡举进士不第,遂高蹈世外,不求进达,恣游名山,自称“三教布衣”。后避乱入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学仙,不知所终。其诗多写山水,也有表现其怀才不遇之情的。《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卷。